在閱讀了費雪在20世紀30年代的這段分析之後,我最近又看到現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的一篇演說稿。羅默在學術界的聲望源於她解釋“大蕭條”的原因,尤其是對終結“大蕭條”的原因。在這次演說中,羅默總結了“大蕭條”爲當前形勢提供的六個教訓。
教訓之一:小規模財政刺激政策作用有限
在發表於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羅默認爲,財政政策並不是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的決定性力量。這並不是因爲財政刺激在本質上無效,而是因爲所採取的財政規模不足。正如羅默所說的,“當羅斯福於1933年就任時,真實GDP低於其正常情況30%多……1934年,財政赤字的增長度達到GDP的1.5%”。
教訓之二:即便利率接近零,信用擴張依然有助於治癒經濟衰退
羅默認爲,實際上,驅動貨幣擴張(金本位制度下貨幣體系的一個特點)的是財政部,而不是美聯儲。1933年4月,羅斯福宣佈暫停美國兌換黃金,並對美元實行貶值。當美國在新高價位_L恢復金本位時,黃金大量湧人美閏,這就可以讓財政部發行與美聯儲票據可互換的黃金(gold certificates)。正如羅默說的那樣,“最終的結果,就是以貨幣和儲備形式的貨幣供應在 1933年到1936年期間年均增長了近17% ”。羅默認爲,這種“貶值帶來的貨幣供應膨脹,打破了探索循環”—這也是支持羅默上述觀點的實證證據。
教訓之三:不要過早壓制市場動力
貨幣供給膨脹似乎給真實經濟帶來了令人矚目的增長:美國經濟在1934年實現了11%的真實增長率,1935年增長9%,1936年繼續增長13%。這誘使美國政府認爲,一切都將繁盛如初。因此,到了1937年,財政赤字減少了美國GDP的2.5%。同時,美國政府收縮貨幣政策,羅默提到,“美聯儲在1936年和1937年分三步將儲備金限額提高一倍”。由此,她得出結論:"1937年的政策錯誤轉向,讓大蕭條又多延續了兩年。”
教訓之四:並肩而行的金融復甦及真實經濟復甦
羅默指出了真實經濟復甦和金融復甦之間密不可分的屬性。這與我們的分析不謀而合:在債務通縮環境下,銀行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根源,它只是問題的表象之一。當前的美國政策似乎只是定位於“修復金融體系”,伯南克的言論足以說明這一點,“如果金融市場和銀行不穩定,經濟就不可能復甦”。這樣的觀點似乎有悖常理,在羅默看來,“強化真實經濟有助幹改苦金融體系的健康。銀行利潤從1933年的鉅虧轉變爲1935年的暴利,並一直延續到‘大蕭條’結束爲止”。
當時,銀行實現盈利似乎更能讓投資者興奮不已。坦率地說,如果一家銀行在這種環境下不能報出利潤,它就會受到投資者的鄙視和遺棄。儘管銀行的盈利環境異常惡劣,但他們很少會因此而喪失流動性。如果你在今天開辦一家企業,那麼,開辦銀行顯然是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選擇。但是,歷史上的慘痛教訓決不可忘記。正如約翰•哈斯曼(John Hussman)指出的那樣,“上一週,投資者還在爲花旗集團前兩個月的經背利潤而激動萬分,但是,這隻能說明投資者很可能並沒有完全理解‘經營利潤’這個詞的真正含義。或許花旗集團已經分崩離析,潘偉迪(Vikram Pandit,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已經在停車場裏賣檸檬,但花旗依舊會報出一個漂亮的經營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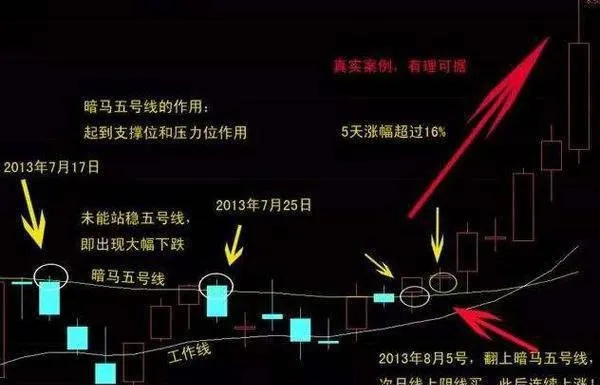
教訓之五:全球擴張性政策面臨壓力
考慮到當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羅默對競爭性貶值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放棄金本位,增加國內貨幣供給,是20世紀30年代世界各閏經濟先後步人復甦的關鍵性因素……這些舉措共同造就了更低的全球(真實)利率……而不是僅僅把通脹從一個國家擴散到另一個國家。”
這也是阿爾伯特和我最近一直討論的問題。我們一直在思考,競爭性貶值(從匯率角度看,它顯然是一場零和遊戲)是否能給本地貨幣供給帶來足夠影響,從而提高通脹預期,最終導致相關國家出現通縮。羅默本人似乎很贊同這種觀點。
教訓之六:“大蕭條”必將永久性地離去
羅默歸納的第六個教訓或許對投資者瞭解當今市場有所啓發。她認爲,“大蕭條”終究要走到終點。正如羅默所言,儘管財產損失令人扼腕,金融市場混沌不堪,信心的喪失更是幾近徹底摧毀美國人對資本主義的基本信念,但經濟最終還是走上覆蘇之路。實際上,1933年到1937年期間的經濟增長,已經達到人類歷史上在非戰爭時期的最高點。如果美國不是在1937年像其他國家那樣,採取令人窒息的遏制性經濟政策……肯定會在“二戰”爆發時實現完全復甦。這不由得讓我們聯繫到,蔓延於當下社會的無病呻吟或許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