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厄姆推崇的第二種方法就是他所說的“盈利能力”法。他認爲:“投資者最想知道的……就是資產在既定條件下的預期盈利能力,即,假設現有狀況在未來期間基本維持不變,一個企業可預期實現的年收益。”他還進一步指出:
它結合了企業一定期間內的實際收益及其按現有基本條件對未來的合理預期。這種記錄必須跨越若干年。首先是因爲,持續的可重複性的業績要比曇花一現的表現更具說服力;其次,較長時期的平均數有利於吸收和平德商業週期對數字的曲解和干擾。
在計算出盈利能力之後,就可以按資本成本進行資本化,從而得到企業價值的評估值,或是將該數值與市價相除,將由此得到的PE與某一類標準進行比較,按照格林厄姆的建議:"16倍於平均收益是投資性購買普通股可以支付的最高價格……如果把16倍的市盈率作爲買入價格的上限,那麼,支付價格應該大大低於這個最大值……10倍的市盈率適用於一般情況。”
這樣的方法操作起來較爲方便。我採用的方法就是利用一定期間(5-10年)內的EBIT(息稅前利潤,又稱營業利潤或經營利潤),然後與前幾年(比如5年)的平均銷售額相乘。這就可以得到正常化EBIT。之後,再扣除利息費用及稅款,便得到盈利能力估計值—整個過程不涉及任何預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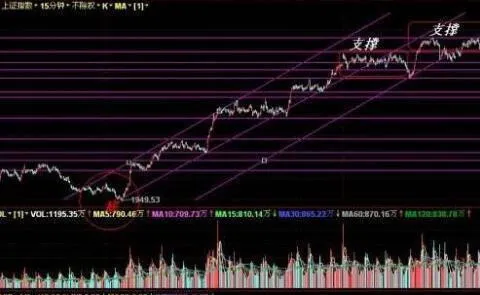
多年以來,很多人對這些方法進行了拓展和深化。要全面介紹這些以價值爲基礎的資產評估方法,我最好的建議還是閱讀一下布魯斯•格林沃爾德的《價值投資》,這本書以當今市場爲背景,對這些歷經時間考驗的方法進行了詳細剖析,並加以延伸,對特許權價值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用三種方法對股票進行估值,但每一種方法都逃不出DCF設下的圈套。雖然說DCF是唯一在理論上正確的估值方法,但它在實施中所需要的假設和預測對誰都是無法企及的。因此,更簡潔、更現實的方法顯然更有可能幫助我們揭開市場蘊涵的機遇,至少可以讓我們不會成爲盲目樂觀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