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實話,我根本就不關心EMH到底是不是學術胭品。但對於EMH的真正危害,凱恩斯早已經一語擊中要害:“許多實幹家自以爲不受任何學術理論的影響,但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
所以,還是讓我們先看看EMH給投資界留下的遺產:首先,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我們將在對CAPM進行剖析和評判,因此,這裏無需贅述該理論的諸多缺陷,我只想再次重申自己一貫的觀點:CAPM是完全多餘的資產定價模型。
對於CAPM,我們在這裏需要着重提及的,就是那些阻礙投資過程的方面—而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又莫過於對業績衡量的過度迷戀。我們至少可以說,阿爾法和貝塔係數的分離是毫無益處的,而最壞的情況下,則會讓我們嚴重偏離投資的真實本性。約翰•鄧普頓爵士對此作出了深刻的評價:投資的終極目標就是“稅後總收益的最大化”。但我們卻沒有緊緊抓住這個目標,而是造就了一個除了對投資者進行分門別類之外一無是處的行業。
正如後來鮑勃•科比所說的那樣:“業績衡量本身是不錯的想法,但在實踐中卻徹底失控。在很多情況下,業績衡量技術的大量使用,反倒阻礙它實現自己的真正目的。”
同樣,對基準對照的癡迷也是這個行業固有偏見的最大來源之一:職業風險。對於主張基準比較的投資者,風險衡量的實質就是追蹤誤差,而這就造就了所謂的“人面羊”(圖1-3)—這是一個只關心自己與他人相對位置的特殊物種。這個物種活生生地印證了凱恩斯的至理名言:“即使以平凡的方式名聲掃地,也好過以不同尋常的方式取得成功。”我們將在下文中討論這種可憐的小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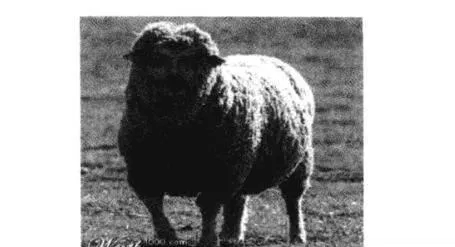
圖1-3 “人面羊”
談到基準對照,我們不能不提一下EMH和CAPM催生的市場指數化。只有在一個有效的市場裏,市值加權指數纔是“最優秀”的指數。如果市場不夠有效的話,市值加權的做法只會導致我們高估最貴的股票,低估最便宜的股票。
在放下風險這個話題之前,我們還要注意到,EMH迷們是如何幫助自己免受價值和動量等不規則事件的干擾。他們以近乎於死循環的方式爭辯道:只有風險因素才能在有效市場上創造收益,因此,這些因素必然只能是風險因素!
而我們這些行爲學學者則認爲,行爲偏差和制度偏差纔是各種不規則事件創造超額收益的根源。我曾撰文指出,無論EMH支持者選擇何種形式的定義,價值股都不會比成長股更危險。
而這種片面強調風險的觀點,又催生出另外一個我認爲完全毫無意義的累贅行業—風險管理。從深層次上看,風險管理採用的技術和工具是有缺陷的。比如說,風險價值等指標只能給人們帶來虛幻的安全。他們更多的只是在追蹤根據短期計算結果形成的輸人變量,但他們卻忘記了,這些模型的輸人變量原本是內生的,根本就不是他們可以左右的。因此,作爲市場因素的函數,相關性和波動性之類的“風險”變量所反映的市場,更像是打紙牌,而不是玩輪盤(即:行爲的結果受制於其他玩家的行爲)。
我們不應該把風險定義爲標準差(或者波動性)。我從未見過一個只做多頭但卻從不關心上漲變動性的投資者。就總體而言,風險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話題—我一直主張,風險三要素是所有投資者都應該關注的東西,即:估值風險、經營或收益風險以及資產負債表風險。
當然,按照CAPM,衡量風險的正確指標應該是貝塔係數。但就像本傑明•格林厄姆指出的那樣,貝塔係數衡量的是價格變動性,而不是風險。貝塔係數可能是分析師計算資本成本時最經常用到的指標,實際上,它也是財務總監們計算類似指標的主要工具。不過,即使是對資本成本,貝塔係數也沒有多大幫助。法瑪和弗倫奇等人收集的證據表明,風險和收益之間毫無關係,這與風險與收益之間理論上存在的正關聯度相去甚遠,更有甚者,當代預測甚至表明,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
這當然也忽略了實際計算貝塔係數時的困難性和主觀性。你採用的是每日數據、每週數據還是月度數據,計算的時間段是多長,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會影響到分析師的計算。帕波羅•費爾南德斯和文森特•貝爾梅霍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最好的辦法,或許就是乾脆把所有股票的貝塔係數均假設爲1.00(這再一次提醒我們,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優雅和完美沒有任何意義!)
EMH還讓默頓•米勒和弗蘭克•莫迪利安尼推導出企業資本結構及股利與公司價值無關的M-M模型。而從業者在實踐中對這些概念的利用,更是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例如,對於那些積極提倡回購、反對股利或是贊成留存收益、反對分配股利的人,M-M假說一直是他們最有效的護身法寶,有了這個武器,他們就可以義無反顧地主張:股東不應該對實現收益的途徑斤斤計較(他們往往會忽略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公司一向習慣於揮霍留存收益,而回購在實質上也與股利相去甚遠)。
同樣,M-M模型強調的資本結構無關論,也促使企業理財者和企業本身加速舉債。按照這個理論,投資者沒有理由關心“投資”的來源到底是留存收益、股權融資還是債務融資。
EMH還造就了另一個歪曲現實的謬論—股東價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概念的初衷,竟然是爲了防止過度關注短期收益。按照EMH假說,一個企業的價值當然就是未來現金流的淨現值之和。因此,股價的最大化也就等同於未來盈利的最大化。遺憾的是,在這個急功近利的現實世界中,這一切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對短期收益的追逐。
但是,EMH最陰險,同時也是最不易被察覺的方面,則在於它以獨有的方式影響着積極型投資者追求增值的行爲。這聽起來似乎有點怪異,但我還是想解釋一下這個貌似矛盾的概念。
EMH迷中的絕對頑固派始終堅持,積極型管理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畢竟已經有人在質疑市場的有效性—桑福德•格羅斯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們的經典論文“論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問號。儘管EMH的超級頑固派絕對不會容忍這些,但他們的論點顯然經不住反證法的推敲: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麼,價格當然就是正確的,而交易量就應該等於零。
EMH的意思表達得很清晰:積極型基金經理可以通過如下兩種方法創造價值。首先是內部信息—但我們可以忽略這一點,因爲這在絕大多數市場上都是違法的;其次,如果能比其他人更精確地預測未來,他們就能在市場戰勝對手,跑贏大盤。
EMH還指出,由於套利者無處不在,因此,機會總是轉瞬即逝的。這似乎和經濟學中的一個傳統笑話如出一轍:經濟學家和朋友走在馬路上,他的朋友突然發現人行道上扔着一張100元的鈔票,他正準備撿起來,經濟學家說:“別撿了,這鈔票是假的。因爲如果是真的話,早被人檢走了。”
遺憾的是,這些再簡單不過的論點絕非玩笑,它們恰恰是EMH這個傳奇中最具破壞性的方面。因爲EMH一直在鼓勵投資者去預測未來。我個人認爲,這絕對是最無聊的一種浪費時間的方式,但也是這個行業中最普遍的現象。在我接觸過的各類投資過程中,約有80%-90%的時間是用來進行預測,但卻找不到絲毫的證據能說明:我們確實能看到未來。
按照EMH假說,機會的短暫性和困擾“人面羊”的職業風險問題,讓人們毫無顧忌地只關注眼前,不放眼未來。通過顯示紐約證券交易所單隻股票平均持有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目前的平均持有期居然只有6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