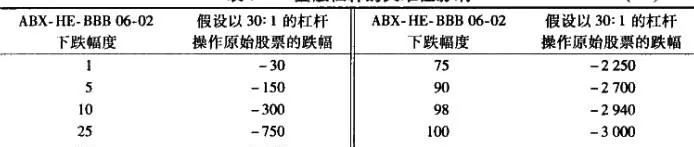薩繆爾森革命。恰恰是強調模仿自然科學進行復雜的量化,而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成爲了主流。在薩繆爾森之前,數學僅僅是基於現實假設的研究的有價值的輔助工其,而在薩繆爾森之後,已經成爲了經濟學的主流。
好的想法往往輕易地被經濟學家忽視,僅僅因爲這些想法不能以高度複雜的統一計公式或是需要用到大址希臘字母的公式的形式寫出。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盆研究,極少在經濟學思想上有所創新往往僅是裝飾複雜的數學模型。而根植於高深的數學推導的糟糕想法,即使其假設經受質疑或是有證據能充分證明其結論有誤,也往往能夠留存。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曾說過:“如我所見.經濟學業巳誤人歧途,因爲經濟學家爭先恐後地以數學作爲華麗包裝,而忽視了真理。”
經濟學想法和原理原是可以被受過教育的讀者所理解的,現在卻變得深不可測,只能爲受過極高數學訓練的研究人員所知。這本來是件好事,如果經濟學已經達到自然科學般的預測水平的話。但是如果沒有切合實際的假設,那麼這門沉悶的科學就會瓦解,而不是更富有生機。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就經濟學偏好使用模型這一點進行過探討:“(運用模型時),我僅僅改變一項似設——該假設考慮的是最完美的信息,通過這種方式使結果顯得合理……(結果)我們成功證明了標準理論並沒有失去生機……僅僅是這一項假設的改變……就得到了驚人的結果.(就此理論而言),這意味餚可以構建一種可供選擇的、有生機的、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範式。”
金融危機和大衰退敲響了警鐘,經濟學和有效市場假說的缺陷被暴露無遺,成千上萬的人追問經濟怎麼會變得這麼糟。質疑聲不僅來自經濟學家和大址的失業者,還來自於《華爾街日報》和其他放任政策派人物。
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最有權力的央行行長們,數十年來都相信
人們足夠理性且市場足夠穩定到可以用一堆等式來總結整個經濟狀況。這些等式被嵌人數學模型,試着去模擬從華盛頓到柏林到北京的多維經濟行爲。但是,這些等式並不奏效。取而代之的是,我們依然遭受着現代史上最爲摘糕的金融危機。不僅僅是有效市場理論在經受着質疑。
這點質疑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消失了。就像約翰·卡西迪在《紐約客》的一篇佳作中所提到的,複雜的新數學理論,例如來自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的理論,導致了新一代的經濟學家開發出更多複雜模型,儘管沒有被接納,但對取代它們也未達成共識。